记者节当天,确山县委宣传部和县融媒体的新闻工作者一行十几人,到一代新闻巨匠范长江罹难地确山县瓦岗镇芦庄村追忆凭吊他的丰功佳绩。范长江新闻实践丰富、新闻思想精深,其人格、其思想、其操守均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今天,让我们再次了解一代新闻巨匠在芦庄的日子,以示悼念。

人物生平
范长江(1909—1970)原名范希天,四川内江人,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八一” 南昌起义。1932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33年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等报撰稿。1935 年后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身份到我国大西北采访,发表了一系列轰动全国的报道,这些报道后来收入《中国的西北角》一书。1937年11月和羊枣、徐迈进等同志创建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即中国记者协会的前身),并被推选为“青记” 的总事。
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他还参加了香港《华商报》的创办工作,担任过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和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等职务。1949年7月,与胡乔木等新闻界知名人士在北平成立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委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
范长江曾经创造了中国现代新闻史上的“三个第一”:他在1935年至1936年间深入西北采访,是“在国内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人”;他是突破新闻封锁, 向国统区报道“西安事变”真相的第一人;他是国内以记者身份进入延安采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并如实报道陕北革命根据地情况的第一人。范长江新闻实践丰富、新闻思想精深,其人格、其思想、其操守均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一代新闻巨匠在芦庄的日子
国家科委确山五七干校1968年开始选址、建设。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一指示被称为“五七指示”。据统计,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及各省共创办五七干校106所,下放干部、家属十余万人,仅河南南部就有中央各部委创办的五七干校三十多所。五七干校选址大多为劳改农场、国有农场、林场所在地。国家科委确山芦庄五七干校就设在芦庄。
1969年3月,被定性为“反革命”、已遭长期关押的范长江随中国科学院首批500名劳动改造和接受锻炼、批判人员乘火车到达河南确山火车站。从确山县城到芦庄没有公路,大家乘解放牌卡车走确泌公路到邢店后,顺河道而下到芦庄,五六十里崎岖的河道和山路,整整走了一天时间。到达目的地时,人们早已疲惫不堪。第一批到达五七干校的人分为两班,一班300人搞劳动生产,一班200多人搞基建。范长江在基建队,主要任务是建房子。
据张威教授介绍,当时与范长江一起送他来到确山的有一名中国科协的工作人员,目前已经95岁高龄。据这位老同志回忆,刚来到确山,范长江表示,“确山我知道。”他对确山并不陌生。但他之前是否来过确山一时间无法确认。
85岁的李长俊是薄山林场芦庄林区职工,是当时薄山林场留下看护山林的五名职工之一。李长俊回忆说,他们这五名职工也住在五七干校院里,为此与范长江等许多人都熟悉。范长江平时不多说话,一有空儿就看书、读报。范长江住在五七干校宿舍南排中间,四人共处一室,睡的普通木床。其中一人不知道是受刺激还是其习惯,每晚休息时,总是一盆水洗了脚再洗脸。另两人似乎不太爱看书报。每当夜晚有书报送来时,范长江自然而然成了四人中的第一读者。

“他爱读《人民日报》,每每看着报纸上的内容陷入沉思。”李长俊回忆,他有一次与范长江说话。“你在这多少年啦?”范长江问。“我1958年就在这儿。”李长俊回答。“你咋来的?”“人家叫我来的。”范长江还特意交代:“不要和我走这么近,对你不好。”
李长俊告诉记者,那时候干校的人还经常到各村义务劳动,劳动结束再晚也不能在村民家吃饭,都回到干校吃。
84岁的芦庄村村民尚大福,是当年芦庄大队加工厂的工人,因加工木材磨锯时砂轮崩裂将右眼误伤导致失明。加工厂与五七干校一墙之隔。尚大福说,范长江除干苦活、脏活、累活外,主要是行动不自由,处处都有人跟着,有空就受批斗。就是排队打饭,范长江也得排在最后边。其他人可以买肉吃,而范长江不能。到夏季,五七干校的人可以到果园和菜园里摘桃子和西红柿吃,也可以到群众家中聊天等自由活动,而范长江不能。每到晚上,五七干校都要组织政治学习和“斗私批修”,范长江也就成了活的教材。范长江站在那里,其他人围坐在四周。要求每个人都要发言,发表对“反革命”的仇恨、对“最高指示”的忠诚。
“我当时也在那儿,范长江谈谈自己的经历,叫啥都做了啥事。他说我入党是周恩来介绍的,你说我反党想说啥就说啥。我不可能反党的。”李长俊回忆,菜园里一年四季的蔬菜有韭菜、萝卜、白菜等,范长江浇大粪的事情是有的,有时候用三轮车推着去菜地,“他是个不小的官儿,至于他会不会感到羞辱委屈,我想是有的。”“1970年,有两个接受改造的年轻人意外去世,其中一个大学毕业生给稻子打药后去洗澡,走到河中间被浪子打翻没能救活。眼睁睁看着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才不幸去世,会不会对范长江的内心造成影响,俺感觉是有这个因子在里面。”李长俊说,一日三餐平淡日常,馒头蔬菜,中午有一顿肉,因为干校种的有果园,养的有猪。“四个人一个屋子,中午吃完饭休息一会儿,然后搬着小墩到地里薅草。”李长俊回忆。
言论不自由,长期的劳动改造,与家人的长期疏离以及对亲情的渴望,看不到希望,一同改造的年轻人的意外去世,凡此种种,不知道哪一个成为最终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确山五七干校大门前五六十米处,有一个菜园子,菜园旁边是一口深7米、直径为1.4米的水井。在范长江刚过完61岁生日后一周,1970年10月23日,早晨起来,五七干校的监管人员突然发现范长江不见了,忙和负责监管他的人一起查找。
“当时没有叫我一起去找,但听去找的人回来说,在菜地边的那口井里发现了范长江的尸体,当时已经浮在水面上了,他穿的还是那身中山装。”李长俊说,“当时他要是想开一点,别背恁重的思想包袱,再有个一二十天干校负责人就换了,被军管了,他也就不会走到投井自杀这一步。”李长俊至今对范长江的死亡惋惜不已。
“干校的人找来几个村民,把范长江的尸体用塑料布裹着,抬到离干校七八百米远的一个山涧阴沟里,草草掩埋了。”李长俊说。四个抬范长江尸体的村民中就有尚大福。
“当时只在山坡的背阴处简单地挖了一个很浅的坑,干校的人就让我们挖土往范长江脸上填埋。我说,不兴土打脸。”尚大福嘟囔着。“可是没有棺材怎么办?”干校的人问尚大福。“我是干这个的(木匠),家里有几块板子。”尚大福在得到默许后就找来几块板子衬在尸体两侧,然后在尸体上盖了一块薄板子就封土了。
我国新闻事业史上一位杰出代表范长江彻底离开了人世。一代新闻巨子以一个这样决绝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976年春天,范长江的儿子范苏苏到确山芦庄将父亲的遗骸移走,安葬在上海西郊青浦区的福寿园墓地。
1978年12月27日,范长江平反大会暨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邓颖超、聂荣臻、胡耀邦、廖承志、粟裕、沈雁冰、宋任穷、史良、季方等同志,分别送花圈和参加追悼会,胡耀邦同志代表中央致了悼词。(本文节选自《天中晚报》记者郭建光撰写的“永远的西北角”)
上一篇:驻马店确山:食品安全宣传氛围浓
最新文章
-
 确山砌体工匠哪家“墙”?这场竞赛见分晓!2023-11-25
确山砌体工匠哪家“墙”?这场竞赛见分晓!2023-11-25 -
 驻马店确山:新闻巨匠范长江在芦庄的日子2023-11-25
驻马店确山:新闻巨匠范长江在芦庄的日子2023-11-25 -
 驻马店确山:食品安全宣传氛围浓2023-11-24
驻马店确山:食品安全宣传氛围浓2023-11-24 -
 驻马店确山:山大老区行 帮扶传真情2023-11-24
驻马店确山:山大老区行 帮扶传真情2023-11-24 -
 遂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退役军人参加驻马店市2023秋季招聘会2023-11-23
遂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退役军人参加驻马店市2023秋季招聘会2023-11-23 -
 西平县举行2023年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2023-11-23
西平县举行2023年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2023-11-23 -
 确山县城管:群众“冷暖”放心上2023-11-22
确山县城管:群众“冷暖”放心上2023-11-22 -
 驻马店确山:“见义勇为主题公园”揭牌2023-11-22
驻马店确山:“见义勇为主题公园”揭牌2023-11-2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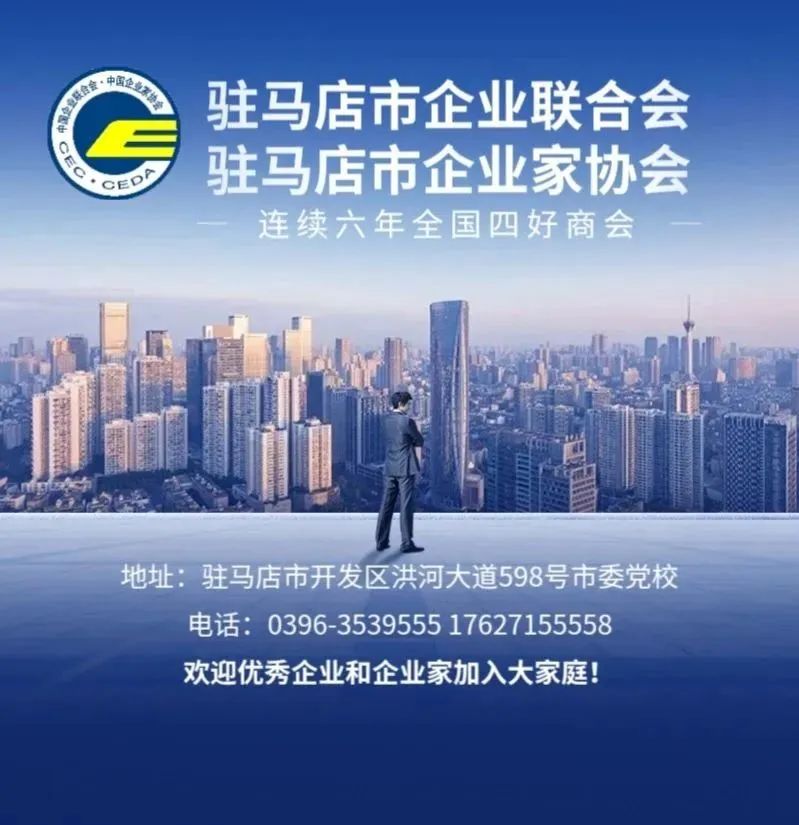 驻马店市企联:以“三服务”为宗旨招募优秀企业2023-11-21
驻马店市企联:以“三服务”为宗旨招募优秀企业2023-11-21 -
 驻马店确山:空气质量 全市第一2023-11-21
驻马店确山:空气质量 全市第一2023-11-21
影响中原








